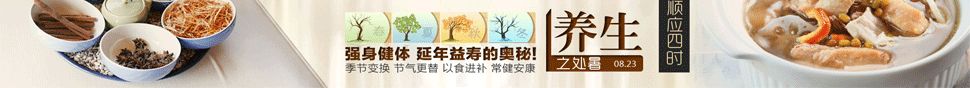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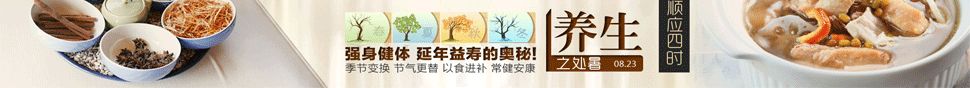
拜读蔡尔辇先生的《追忆泉州开元慈儿院》一文,(载《泉州文史资料》第十六辑,觉得还有下文可续,特草此文,以供关心开元慈儿院院史者,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。同时,也为我那远逝的童年,留下一点印迹。
看来,蔡先生是我的学兄。他于年入院,于年毕业离院。我是年入院,年离院。他离院,正是我踩进院门之时。他出我进,虽是院友,却彼此从未谋面。蔡先生离院后的6年间,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,院情是国情的一个小缩影,此时的开元慈儿院,当然也处于最艰难的时期。与蔡先生文中所述的院情比较起来,此中确有不少变迁。
我为什么能够入慈儿院?8岁时,父母不幸因病双逝。那时,我在泉州的亲人只有姑母,外祖父、母,以及守寡的伯母一家人。伯母多子女,仅靠衲鞋维持一家大小生计;姑母寡居,四处上亲戚家帮工糊口;外祖父杨冬舍,花桥宫善举公所的耆宿大都认识他。他长期在公所里办事,仅靠他一人收入维持一家四口人生活,家境可想而知。外祖父去世后,外祖母带着我妹妹捡菜叶、领救济粮度日,日子更是难熬。
好在姑母从小疼爱我,几乎天天蹇动小脚,四处央求,求到亲戚黄叔梓(泮宫口同益布庄股份经纪人)鼎力赞助,出面与院长叶青眼商量,由黄叔梓先生出钱(聊充我的伙食费用吧?)才送我进入慈儿院。此时的开元慈儿院,经费拮据,大非昔比。全院只维持原有三个班院生就养,再增收一个孩子就十分困难。一般都要像我一样,有人(或单位、机构)出点钱才能入院。我曾读过私塾,可插入居中的那一班。最高的那一班,就像蔡尔辇先生文中所说的,班内有几个是年龄偏高的,有的约莫有20岁上下吧,真如泉州俗话所说的:“大如堂,小如豆。”最低的一班,同我就读的那班近似,年龄相对较为整齐。
该院一概收男不收女,院外人称它为“和尚院”。加上我们院里学生自理头发,人人光头一盏,这“和尚院”的戏称,也就“名副其实”了。自改院名为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之后,曾破例招进了为数不多的女通学生,而且,也聘来了两位女教师。院名是徐季元任晋江县长时改的。徐氏是蒋经国先生任赣南专员的属官,莅临晋江之初,带来了蒋氏新赣南之风,颇有一香“新政施”。例如在开元寺东侧办了军属卷烟厂,在承天寺内办了大众食堂。前者是为军属开了就业的门路;后者是为贫者免费施粥,日给两餐,我曾随我外祖母、妹妹到承天寺吃过,佐餐的菜(或盐)自备。那一大锅太稀的稀饭,教我联想起游泳池。虽然如此,能吃到米粒儿,就很值得称幸了。
作为徐县长“新政”的一件事,就是将开元慈儿院收为县办。为了此事,徐季元曾来到我院,对叶院长作疏导工作,叶院长和董事们都不同意。不久,院名却改为“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”,并对外招收男、女生,都是通学生,只教不养,酌收学费。名副其实的既教又养者,就是我们这些老院生。至于为何要改院名,为何要破例招收男、女通学生,直到今天,我还一点也不知道。不过,徐季元被地方势力撵走后,一直到解放初,这新院名就这样被改定了,不再恢复旧院称。
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旧址——虎豹楼
慈儿院当然以收容失去双亲的孤儿为主。此外,还招收什么对象?这是很难截然界定的。举几个我所知道的例子来说吧。有一个名叫赖自达的,他父亲被抓去当兵,母亲还在。母亲生计无着,家境困窘,日子过不下去,常携着自达和他的弟弟,到县政府闹堂。人家要把她轰出来,她就躺倒。人家把她拉到大街上,她就躺在大街中,哭哭啼啼,骂骂咧咧。现在想起来,那恐怕是穷妇技穷的一招了,要是日子挨得下去,谁会弄出这一着呢,实是事出无奈。不过,后来,这赖自达就进开元慈儿院来了,她母亲还常常来看他。
有一个名叫陈自强(连这名字也是院里给他起的),从小当乞丐,栖身破庙中,是慈儿院疏散乡村时,把他收容来的。
有一个名叫王金长的,听人家说,他母亲杀死他父亲,投尸于百源清池。案破后,他母亲投入囹圄,他成了无依无靠的不幸儿。就这样,进到慈儿院来了。
还有一个名叫释传接,是年青的小和尚,桀骜不驯,被送入慈儿院教教乖。但他年纪大些,气力足,手脚还有点儿拳路。一进院,常打人,屡被告到院长那里。
另有几个,是教师、保姆的子弟,随父母入院读书。他们衣着整洁,但家境也不好。一投入这个苦孩子的大熔炉来,跟大家一样,没有什么优越感可言。
院里生活很苦。以三餐来说吧,我初入院时,还可吃到粥;后来,只有中午吃粥,早、晚都吃麦皮(泉州话叫“麦铺”);再往后,三餐都吃麦皮。没蔬菜时,桌上只摆着一碗盐,让大家拌着吃。8人一桌,有桌长。桌长夹菜,桌员看个样,夹多了,桌长匀少点,直到桌长看平均了,才各自放进饭碗里。不过,也有的是由桌长一巡一巡地夹到各人碗里。粥(或麦皮)是怎样分的?记不清楚了,似乎是按勺分进各人碗里的。
初时,有一个台湾籍的老工人,专管菜园。后来,逐步开地种菜,每个院生都要轮流浇菜。菜园收成时,大家都有菜吃,有时干脆吃菜粥。收成多时,或切丝晒成菜干,或者腌成咸菜。院里有桃树,多是苦桃,捣碎,腌成咸桃脯佐餐。木瓜切片、切丝,也是菜,而且算得上是“好菜”。木瓜树倒了,去树皮,取树芯,切成丝,也是菜。香蕉树倒了,去树皮,取树芯,切碎,也是菜。苋菜,吃罢叶,苋干腌咸,也是菜。芥菜、菜花、高丽菜,以及蕃薯煮咸,称得上是上等好菜了。慈儿院的教师一无例外地要素食。如果你想尝点肉腥味,就得走出院门以外,院门以内,都是院规实施的范围。
不过,教师有教师席(只有一张桌子,可见当时院内教职员不多)。席上,每餐都有四碟素菜,另有一桶粥或饭(两稀一干)。膳堂里,学生早吃完了,但腹里还空虚,有的孩子就在等着。一觑着了最后一位老师吃完离座,都一轰而上,或用手抓碟菜吃,或用勺舀饭吃,甚至碟里的菜汤,也伸长舌,舔个精光。
记得弘一法师在泉州去世时,全院曾集队到承天寺为法师念经。那天中午,吃了一餐汤面,这是法师治丧机构送来的。在那时,这一餐可算是院中的最好美食了。此外,过年当然也有个过年的样子。我记得,有一年正月初一,我们院里曾吃过线面和冬至丸煮成的线面汤。这碗线面汤,也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。
弘一法师
院内有保姆,此时只留两人。年幼的孩子与保姆住同室,由保姆略加关照。听说以前衣服髒了就换给保姆洗,缺衣服还可由院方发给旧衣。这福份,我们领略不着了。我的衣服,一般是我姑母向亲戚讨来的。比如陈盛明先生,他的子女年龄大体与我相差不远,可讨来几件合身的旧衣服。在别人看是旧,在慈儿院孩子看,却是令人称羡不已的时装,非到过节、作客、上街是舍不得穿它的。髒衣服要自己洗,破衣服要自己补。保姆得闲,你也可以求她补几针。至于洗衣服,两个保姆就照应不了啦。保姆要洗被单,浇菜,切菜丝,腌莱,制豆豉,腌酱瓜……有的孩子,或怕冻,或懒,或遗忘,髒衣泡在水里久了,发臭,生虫,以致于衣服烂了,那也是常见的事。加上洗衣用的是淡尿水、稻草浸成的薄硷水,衣服很快破烂。即使寒冬,孩子们穿的也只是一两件薄衣。棉衣、羊毛衣,谁也没穿过。天一转冷,大家都被冻得双唇发紫,上下牙打战,浑身直哆嗦,鼻流清涕。一下课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冲往厨房,或捂近灶台,或背靠烟囱,或双手贴近灶火。总之,此时的厨房,确是御寒的好去处。小小的厨房,顿时提高了“人口密度”,被挤得水泄不通。
有时遇到全市性的集会或游行,怎么办?一般是由院方借给每人一副童子军装,事完之后,照旧收藏起来。有次,也许就是国民党政府省教育厅长徐箴来院视察的那一次,院方十分紧张,在筹划迎接厅长事宜中,有一条是如何隐蔽“有碍观瞻”的事物。那一天清早,院方宣布了一份名单,叫这些人到后庭去,不许跑出来。这些人就是一些衣衫褴褛、瘌痢头、生疥疮的孩子。
按院规,院生不准走出院门,尤其不许上街去。有一度,泉州流行鼠疫、霍乱、染上鼠疫的那家门口,都用石灰粉撤了半圆圈,气氛恐怖。那时候,院门索性关死了,轮流站岗。因此,倘若肚子饿得慌,也只能在院内想想办法。办法倒有不少,就靠各人神通。头上,有果树;脚下,是菜畦,都有可供充饥的食物。龙眼成熟时,好几棵是“正东壁”的,核小,清甜,带有蕉油味。年大的,可以上树摘,年小的,在地上扔石块,也可捡着几颗解解馋。要是遇上刮大风,下暴雨,能捡吃的东西可多呢,龙眼之外,还有木瓜、柚子、枣子、桃子等。
水果产期过了,菜园里可吃的东西并没过时。花生收成后,有的孩子拿起锄头,翻捡地里剩下的花生果;蕃薯长大时,挖它一两块生吃,也满甜美的。再不,高丽菜收成后,地里留下那么些粗根,用刀片剜芯吃,味道也不错,“穷则思变”一语,在这里,是应该给予补充注脚的。人到那样的地步,总得想点变通办法。对于生活如此穷困的苦孩子,我们怎能求全责备,苛求他们拘守绳墨呢?
泉州开元慈儿院与创始人圆瑛法师
开元慈儿院的经费,大多来自于募捐。国内募,远隔千里的南洋各地也去募。我们膳厅有一块横匾,上写“沪上仁风”四个大字,两旁刻有上海乐捐者的姓名、金额。在泉州,吴桂生、周骏烈等先生,都十分关心慈儿院的经费来源。我在院的5~6年期间,叶青眼先生曾到南洋募捐两三次。他一出门,院务交由他儿子叶禽择负责。我们住宿的那幢两层楼房,本来正中楼有“胡文虎先生捐建”七个大字。这幢楼直到今天还在,就在院门左侧、操场的旁侧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侨汇中断,海外募捐一一此路不通。国内富裕者也不多,当时,晋江一带的“番客婶”甚至不得不扯下脸皮,摆地摊,变卖故衣,当首饰度日。很明显,靠募捐维持开支,已是不可能了。怎么办?时青眼院长提出,全校师生组织起“自力更生,万金生产团”。先于校内,开设粉笔厂、薯粉场、簿本工场、泥塑场。记得当时还请来了一位西街佛雕店的师傅。但到后来,仅存的就是粉笔、簿子两项。粉笔用石膏粉作原料,太粗、太硬,伤了黑板,而且字迹不白,难于销售。簿本是用木刻板作底板印成的,油渍不匀,不精美。这两项,基本上自产自用而已。
后来,终于在新门外找到一块面积颇大的沙地,这“自力更生”才算成了点气候。院方雇了一个年青体壮的庄稼汉,名叫亚辉。还购置了一艘小渡船,一枝鸟枪,筑起了一座高草棚。上午,照常上课;下午,步行过渡到农场劳动。亚辉会耕地,会开枪,会划船,还会点木作。
农场种甘蔗、蕃薯、花生及少量蔬菜。庄稼成熟时,院生分批轮流住农场,就宿在高草棚里。叶青眼长子叶禽择也同我们一道住过农场。全农场只有一盏马灯,四周漆黑黑的,光坐在棚里听夜,实在难熬,叶老师就给我们讲起了《天方夜谈》故事。故事讲得很吸引人,听完一个,巴不得接着听二个、三个……农场之夜,变得很有魅力了。白天在地里干活,就巴不得夜晚赶快来临。
那年年景很糟,生计无着的人很多,有人趁夜黑出来偷挖蕃薯。夜黑偷挖蕃薯风险也不小,一怕被人抓着;二怕被老虎咬死。有人蕃薯吃不着,自己反被老虎充当美食。我们守农场,主要的防盗贼,万一遇着盗贼,那也不过是吓退吓退或者规劝规劝而已,不会拿他严办,因为他毕竟也是苦命人呀。
院生对办农场是欢迎的。因为,一则日子好过多了,有蕃薯吃,花生、豆类收成时,还有花生果、大豆、豌豆下饭。二是老被关在院内,趁半天上农场的机会,也可一路上看看这外面的世界。三是农场的东西是自产的,折几支甘蔗尝尝,挖几块甘薯烤吃,也不致于像以往限得那样死。四是农场生活丰富多彩。活干完后,还可趟进溪水泡泡洗洗,院里生活从没有如此写意过。但,苦也是非吃不可的,别的不说,光说从农场挑东西回来,那肩膀就常被磨得又红又肿又痛。路又不短,来回两趟,准叫你双腿痠痛,走难走动,蹲难蹲下。要是被太阳晒黑起泡,连晚上躺床都会叫痛不迭。
有一年,大概是日寇侵犯福州的那年吧,开元慈儿院疏散到南安雪峰寺。不论大小,人人都步行到达。随着我们一齐到达的是劳动工具。照样半工半读,半天上山砍柴,半天读书,大忙时,白天劳动,夜晚挑灯上课。砍柴按定量,不达定量者,开饭时,点名站在中间,等到人家吃过一半时,老师才叫你入席。孩子们倒很讲义气,砍多点的同学,也很乐意地把多出来的量,拨给缺量的同学,凑足了数,免得缺量的同学受罚。
砍柴捡叶,做惯了也不怎么的,最怕的是渴了没水喝。有一次,我上山收工回来,渴得难耐,到处找水喝,一见着坛坛罐罐,就掀开看看。有一个陶坛子,看不出内中放的是什么,就用鼻子嗅一嗅。这一嗅,把坛里的污气吸进了。我病倒了,而且病得很重,以致于疏散返院时,只得坐在箩筐里,让农民挑回泉州。回院后,院长不得不通知我姑母,领我出去疗养。原来,那坛里放的是骨灰,也不知封了几多年了。
开元慈儿院的课程设置,与普通小学差不多。不过,美术、劳作、体育三科常常没开课,实行半工半读后,这三科,更是无法挤入课程表。不管课程怎么挤,那晨会、晚会却是少不了的。纵令节日、假期,晨会、晚会仍须照常。晨会、晚会,就是令大家集中在礼堂(大热天移到操场)念经,由值星教师视督。讲台有佛桌,佛桌置大理石释迦牟尼塑像,以及香炉、引磐、木鱼,桌旁有一副钟鼓。桌前、早、晚会三位主事各司一职(均由院里学生自动担任),中间一人执引磐,负责起调及领诵;左侧依节奏敲钟鼓;右侧叩击木鱼。不必专门训练,一般老院生都会这三事(每日两会,听多了自然就会了),按仪式,每次都从《炉香赞》起始:“炉香乍热,法界蒙熏,诸佛现全身……”《三皈依》结束。至于中间念的什么经文,就略有变更。或念《金刚经》,或念《华严经》,甚至也曾念过《太上感应篇》。《太上感应篇》该是道教经文,为什么也放进来了?然而,说怪也不怪,徐季元任晋江县长时,我们也于晨会后念《新赣南家训》:“东方发白,大家起床,洗脸刷牙,打扫厅房……”而且《新赣南家训》全文抄录,贴在黑板上。反正,该念什么,什么时候换念什么,都由叶青眼院长指定。
叶青眼院长偶尔也来参加。他来参加,大概会后有话要讲了。有时讲佛理,有时讲佛教故事,有时讲院内要事,有时甚至讲起八股文的作文要领。
叶青眼院长
叶青眼这三个字,辛亥革命初是十分响亮的。他,是闽南辛亥革命的著名志士,与许卓然齐名。但后来对革命消沉了,消沉到几乎判若两人。记得有一次,辛亥革命老人丘廑竞,手执一面小小的国民党党旗,到处讲演,来到慈儿院时,叶青眼也不太热情,只安排丘上台作一次演说。演说时,叶院长连在台上陪坐都没有,不知道作何托辞溜之大吉了。叶青眼是清朝廪生(是清代资历较深的生员),但后来却是闽南辛亥革命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。此时,为什么对我们讲起八股文要领呢?叶院长反对我们嬉戏玩耍,蹦蹦跳跳。孩子们哪能不蹦不跳不叫呢。或跳格子,或踢毽子,或跳绳,或“过五关”,或玩“救国”,或独脚对撞……一玩起来,少不了吵吵嚷嚷。叶院长一听着,悄悄地拿起竹鞭,一见人就鞭,不论你是参加还是旁观。一边鞭,一边骂:“国难当头,不去读书,还只顾玩耍!”有时他不鞭也不骂,悄悄地叫那些玩耍的孩子,去干点“国难当头”的“正经事”——拔草、扫地、挑水、收拾晒场的谷物……
叶院长一出院门,特别是当叶院长往南洋募捐之时,全校师生都松了一大口气,院内的气氛也显得异常活跃。叶院长出外募捐,由他长子叶禽择先生代行院长职务。此时,操场、天井、走廊、膳厅、礼堂、西塔里外,都是玩玩跳跳的地方。没有什么体育设施,也不碍事。操场两端,各摆石块或砖块当作球门,摘一颗柚子,或用碎布扎成球形,便可踢起足球来。用薄纸穿古钱眼,制成毽子。只要有一条草绳,便可以跳绳。至于跳格子,“过五关”等等,更便当,只要拿一块瓦片,在地板上划划线就行了。
也许平素有了这样一些蹦蹦跳跳的基础,加上孤儿特有的好胜争气心理,不怕跌、撞的勇猛劲,当我们与西隅小学、新隅小学比赛足球时,倒能赢了几场呢。老师们组织的排球队也不赖,也曾赢过友校的教工队。不过,好景不常,一当叶院长临近回院之前,那些新置的体育器材,就得采取紧急收藏,院内又恢复以往的沉静。
如果说,叶院长对体育也曾提倡的话,他就只提倡拳术一项。他曾请来了拳师,教过我们打拳。我们同学中间,就有一个拳师的儿子,他既是学生,又是教习拳术的先生。不过这学生似乎熬不过这里生活的苦,不久就辍学离院了。
院长之下,设有三个主任:教务主任、养务主任、总务主任。那时,教务主任是黄沧江,也是慈儿院院友,读了简易师范后,回院工作。养务主任是刘蔚霞,多年一直教我们的国语。总务主任是姓赖,教我们算术。
我们这些孤儿,独立生活都较强,一般不太需要养务主任过于操心。院里不设医务室,也没有专任医生,只有一个会计,他粗略有一点中医常识。孩子伤风感冒当然常患,但我们都听之任之,不几天也就好了。劳动受雨淋,喝点姜汤、盐水,也就没事了。肚子痛,顶紧床沿,捂紧棉被’也没事了。最伤脑筋的是,打摆子(疟疾)。发冷,发热,闹了两场,就面黄肌瘦,有气无力。不过,叶院长介绍一种青草药,叫虎爪草,叶呈虎爪状,院内花盆里种了几棵。孩子一患此病,就自找虎爪草,捣成泥,贴在手脉上,第二天,手脉处起水泡,也就好了。
我在慈儿院五六年间,只见到一个名叫王文华的,因吃生花生仁,患了痢疾,吃药好不了,病死在慈儿院。其他院生,都长得好好的,陆陆续续走向社会。如果我们头发长了,院里有剃刀。先把头洗得湿透,再央求一个同学用剃刀刮。技术不高明,有时可能刮伤了头皮,留下一道道血痕,但总比蓬头垢面好多了。三餐吃不饱,也各有各的办法。有的同学自寻那房前屋后的空隙地,种了几棵玉蜀黍、南瓜、豌豆……改善改善个人生活。碰到节日,我们也会自筹过节的事,比方说八月十五前,我们都忙于抬干柴,捡干叶,拾龙眼核,动手砌起“中秋塔”,中秋节一到,大家都分别在自己的塔前,烧塔过中秋。
5~6年的开元慈儿院童年生活,至今回想起来,还饶有兴味的。我是年秋抗战胜利时,离开慈儿院的。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些天,泉州市热烈庆祝的盛况,至今记忆犹新。那些天,开元慈儿院也开了禁例,允许院生上街看热闹,开开眼界。
离院后,我一直读到华东师范大学毕业。如今,我是漳州市地方志编委会总编辑,被评为副编审职称。心想,我能有今天,无论如何,是不应忘记开元慈儿院的年年月月的。年,当我第一本书在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时,我首先付邮寄赠的就是——我的母院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
